客家族群认识论转向与学术知识体系建构
时间:
[摘要]客家是我国汉族的一个重要且独特的支系。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客家研究中,对于“什么是客家”这个客家研究的根本问题的认识与解答,经过了由“民系论”到“族群论”再到“文化论”的多次转向,每次转向都激发着学者们对客家研究的热情,不断推动客家研究的广泛和深入开展,使得客家研究走过了由停滞到复兴再到快速发展的历程,在研究内容上,从客家历史源流扩展到客家文化多维领域;在研究方法上,由历史学为主向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方法转变;在研究走向上,从对客家历史文化的探究转向对客家历史文化的挖掘与客家当下文化发展并重。在每种观点引领下,客家研究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其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亦存在差异,并分别发展成为不同的客家研究路径,共同丰富着客家研究的话语体系,不断推动客家研究学术知识体系的构建和逐步完善。“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的观点使客家研究趋向建构一个更具广泛意义的学术知识体系。客家研究可以加强和深化对中国社会历史整体性的理解和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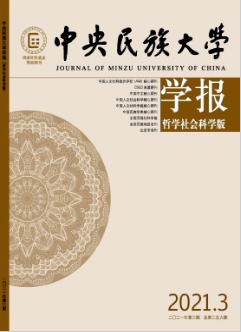
[关键词]客家研究;理论范式;学术知识体系
自1815年徐旭曾《丰湖杂记》问世以来,客家研究至今已走过二百余年的历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样貌,其中有跌宕起伏,有高潮低谷。以1933年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问世为标志,客家研究进入了严格意义上的学术阶段,体现出与之前一百多年完全不一样的发展逻辑。客家研究从弱小发展壮大,研究主力从中国扩展到国外,再从国外回归到中国,形成了较庞大的客家研究队伍和主流阵地,对客家研究领域内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不断开拓客家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从对单纯的客家历史和方言研究走向对客家文化的多元全面研究,不断构建和丰富客家研究的学术知识话语体系,学术影响力逐渐增大,日渐成为一门具有世界影响的“显学”。
为厘清作为一门学问的客家研究的发展历程,总结得失,把握规律,更好地推动客家研究在进入新时代以及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繁荣发展,我们很有必要对客家研究做一个全面的回顾总结。基于此,本文在对1949年以来客家研究主要成果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选取客家族群认识论的视角,也即是从如何认识和界定“客家”或“客家族群”这一客家研究的最基本概念着手,全面总结梳理客家研究的发展历程,并深入勾勒和分析客家研究学术知识体系的构建过程。
一、客家研究发展概述
为更直观地展示客家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取得的成绩,基于资料收集和数据统计的便利,本文重点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客家研究成果进行分析。
(一)客家研究成果梳理
在中国知网上,以“客家”作为关键词在期刊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录得客家研究论文10271篇(数据检索截至2020年8月31日),将检索所得数据,根据相应年份制成客家研究论文刊发柱状图,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客家研究论文总体呈上涨趋势,且呈现出三个非常明显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9—1979年的30年间,仅有18篇客家相关文献,但是据检视后发现,可能由于年代久远的原因,数据库记录并不准确,经过逐一查证,发现这18篇文献中真正关于客家的仅有5篇,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1958年发表于《戏剧报》上的两篇关于客家戏的介绍文章,二是1960—1961年间发表于《文字改革》上的3篇关于客家方言的文章。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仅有的5篇文献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客家研究论文,最多只能算客家知识介绍。其余的13篇文章几乎并不涉及客家,甚至与客家毫不相干。从这30年间仅有的5篇客家研究文献来看,客家研究在此阶段完全处于停顿状态。
第二阶段是1980—1999年的20年,随着1978年国家的改革开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迎来了春天,客家研究也逐渐复苏,研究成果逐年递增,至1999年间共刊发论文891篇,其中1980—1989年153篇。《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刊发的罗美珍《畲族所说的客家话》和《韶关师专学报》1980年第1期刊发的饶纪洲《漫话粤北采茶戏》两文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开客家研究风气之先的成果,承袭着之前的客家方言和客家民歌两条研究路数,也引领着彼时客家研究的整体走向。1990—1999年,客家研究迅速发展,论文数量达到738篇。虽然研究内容仍然是以客家方言为主,但是对客家历史源流、客家山歌、客家风俗、客家精神、客家建筑等亦有所涉及,客家研究范畴不断扩大。客家研究呈现出即将全面开花的态势,这也预示着客家研究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将会迎来大发展。
第三阶段是在21世纪的20年里,客家研究论文更是获得爆发性增长,达到9362篇,年均400余篇。在研究内容方面,更是涉及客家的方方面面,并涌现出一大批客家研究高产学者。
在客家研究著作方面,通过以“客家”作为书名关键词在读秀数字图书馆进行检索,录得著作1632部(数据检索截至2020年8月31日),按照年份制成客家研究著作数量柱状图,如图2所示。
相关期刊推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创刊于1974年,本刊是哲学社会学术理论刊物,宣传、阐述党的民族政策,开展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研究。
由图2可知,客家研究著作尽管在数量上呈震荡走势,不过大体上还是呈现出与客家研究论文相似的阶段特征。首先是1949—1979年的30年间,一共出版了21本客家著作,其中1949—1959年间出版15本,虽然相比该时期的客家研究论文的数量要更多,但仍然局限于客家方言与客家山歌两方面。1960—1969年,则只出版了3个版本的罗香林编著的《客家史料汇编》。1970—1979年同样也只有3本,内容分别涉及客家方言、山歌和俗文学。1980—1989年,客家研究著作逐渐增多,达到38本,不过主要还是关于客家山歌民谣等。但是此时期罗香林《客家源流考》(1989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和《客家研究导论》(199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再版,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客家研究成果的引介(如邓迅之的《客家源流研究》,1982年,中国台湾天明出版社等),说明客家研究开始显现复苏迹象。1989年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卫东和王洪友主编的《客家研究》(第一集),将1933年《客家研究导论》出版以来55年间的国内外客家研究重要论文及资料汇编成集,对既有成果的总结梳理,开启了客家研究新的篇章。1990—1999年,客家研究著作达235本,内容逐渐走向多元。进入21世纪后,客家研究著作快速增长,至今已出版1341本,年均出版量维持在70本左右,研究内容涉及客家各个领域。但是根据图2,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自2015年客家研究著作接近100部的高点后,正在逐渐下滑。
(二)客家研究发展历程
根据上文对客家研究论文和著作的梳理可知,客家研究70年来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三个阶段。一是1949—1979年间,国内客家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国外客家研究虽有零星成果,但影响甚微。二是1980—1999年间,国内客家研究开始复兴,出现一批较有影响力的客家研究专家和客家研究成果,对客家研究中的重大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与此同时,国外客家研究也相应地有所发展。三是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客家研究迎来了极大发展,从事客家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得到不断开拓,研究成果呈现爆发式增长,中国国内毫无疑问地成为客家研究的学术重心。
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自1949年以来的客家研究整体上呈现出停滞、复兴、蓬勃发展三个鲜明的发展阶段。但是客家研究70年间所出现的这种鲜明的阶段特征,仅仅是因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及2000年进入21世纪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革等这样的“社会事实”吗?当然,毫无疑问,社会变革的外部政治经济或文化因素必然会对人文社科学术研究构成强力影响,客家研究自然也不例外。那么在外部社会政治经济影响之外,客家研究发展中出现的这种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还有没有来自其自身内在的原因呢?又或者说,是否有客家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或原因等,从而导致了客家研究在内外因合力作用之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呢?
经过梳理,笔者认为,1978年的改革开放与2000年进入21世纪的特殊时间节点的“社会事实”是客家研究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特征的外部因素,内部学理性原因在于,客家研究中对于“什么是客家”这一问题的回答和对“客家族群”的认识界定这个根本理论问题的认识论转向。也即是说,特殊历史节点上的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刺激了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展开对于“客家”或“客家族群”的认识与界定,而对于“客家”或“客家族群”这一客家研究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概念的不同认识,从内在学理上推动和激发了1949年以来客家研究的发展并使其客观上呈现出明显阶段性特征。可以说,对“客家”或“客家族群”认识的发展与深化,正是1949年以来客家研究不断发展的内生动力之一。客家研究在不同阶段所展现出来的不同侧重点以及不同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乃至所构建起的相应的学术话语体系,在根本上来说很大程度上都是建基于对“客家”或“客家族群”这一根本概念的不同认识。因为进行客家研究,首要之义就在于必须明确我们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正如王东所认为的,研究客家必须首先面对“什么是客家”或者“客家是什么”的范畴性问题,也即是如何界定客家[1]。对客家研究中这一根本问题的不同理解和认识,将直接指向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等,并最终形成不同的研究走向;而每次针对“什么是客家”这一问题的新理论观点的出现,总能给客家研究带来新的学术活力和新的话语言说方式,激发学者们展开客家研究的新一轮学术大讨论,这种大讨论往往带来的是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学术发展高潮,推进和丰富着客家研究,使得客家研究呈现出新的话语范式,并逐步构建起相应的学术知识体系。
在对“客家”或“客家族群”的认识和界定上,学界大致经过了“民系论”“族群论”和“文化论”三种理论的发展转向。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以罗香林为代表所提出的“客家民系论”,明确认为客家是汉族的一个支系。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以梁肇庭等为代表提出的“客家族群论”,使客家研究从罗香林的“民系论”模式转为“族群论”模式。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谢重光等为代表提出的“客家是一种文化概念”的观点,客家研究从“族群论”视角转向“文化论”视角。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客家研究中对“客家”或“客家族群”认识论的转向,在时间节点上与前文所分析的客家研究所呈现出的三个阶段的时间线大致吻合,且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在客家研究的“停滞”“复兴”和“蓬勃发展”三个阶段中,对客家所展开的研究几乎大致对应地分别侧重于上述的“民系”“族群”和“文化”三大视角。由此可以看出,1949年以来客家研究所呈现的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在某种程度上与客家研究中对“客家族群”这一基本概念的认识和界定的不同是密切相关的。
对“客家族群”的认识和界定的每一次转向,都给客家研究开掘出了新的研究空间和构拟了新的话语言说方式,并推动客家研究在新方向之下的学术知识体系的发展与构建。
在“民系论”影响下,客家研究主要集中在客家历史与客家方言等方面,研究方法和话语方式也以历史学与语言学为主,其最主要的目的在于从历史文献或语言传承两个维度深入论述“客家是汉民族一个支系”这一基本命题,试图找寻出客家与汉族的某种内在一致性或传承性,藉以从“异中有同”的角度打造出客家的立身之基,以此提升和扩大客家的影响力。在此种话语言说方式之下,客家研究构建出了基于“民系论”下的客家历史和方言研究的两足鼎立的学术知识体系。
在“族群论”主导下,客家研究从以往注重客家的历史渊源、方言习俗等客家文化具体事象转向客家族群意识、族群认同、客家与其他族群的比较研究等客家“族群性”、主观性的文化建构,而研究方法和话语方式也以人类学、民族学等为主。“族群论”主导下的客家研究不再单单着眼于论述客家与汉民族的“异中之同”,而是回归到了客家本身,重在彰显其独具特色的“客家特质”,更多的是突显客家与汉民族或其他族群间的“同中之异”,试图通过差异法视角来构建客家的主体意识。因此,在“族群论”的视角下,客家研究更侧重于挖掘和表现客家与众不同的独特气质。围绕着客家独特的“族群性”这一核心议题,学者们展开了对客家族群的文化建构、客家与其他族群和不同客家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借用民族学和人类学等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相关理论等,逐渐构建了更加多元化和丰富的客家研究的新的学术知识体系。
如果说“族群论”引领下的客家研究是对客家主体意识的追寻与回归,是通过差异法来挖掘和彰显客家的“族群性”的话,那么“文化论”视角下的客家研究无疑是对客家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更宏观层面的文化价值的全方位深入开掘和更广阔天地的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文化论”认为“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客家文化不仅是族群文化,也是一种地域文化”,这就将客家研究放大到了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之中,使得客家研究冲破了之前“民系论”和“族群论”视野的局限性。也即是说,此阶段的客家研究不再局限于历史渊源、客家方言、客家民俗、客家建筑等客家作为汉民族支系的特征和族群特性等方面,而是跳出“民系”和“族群”的范畴,从更宏观和更抽象层次的“文化”角度入手,着眼于客家文化的精神内涵、外在表现、保护利用、创新发展、产业活化等,逐步从客家文化的挖掘与建构以及当前客家文化的创新发展等维度,整合和构建起文化学视野下的客家学术知识体系,比如对客家地区当下的文化遗产保护、文化旅游、文化发展、文化创新等的研究等等,都正是在该学术体系之下得以展开。
综上,客家研究经过从“民系论”到“族群论”再到“文化论”的两次转向,不断深入发展,逐渐成为一门相对独立与自足的学科,构建了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与学术知识体系,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在“客家族群”三种不同认识理论的推进之下,客家研究领域不断得以开掘和拓展。目前而言,不论是客家源流、客家民俗、客家方言、客家妇女、客家旅游、客家教育、客家民居、客家民间体育、客家民间文献、客家民间文学、客家民间音乐、客家名人、客家饮食等具体文化事象,还是客家族群认同、族群意象等客家“族群性”建构,抑或是客家文化遗产、文化旅游、文化产业等客家文化的创新发展等,凡是关涉客家的方方面面,都被纳入客家研究范畴之中。那么,目前这些客家研究的广泛而丰富的学术谱系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建构起来的,客家研究又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呢?对“客家族群”的认知转向又是如何推动了客家研究学术知识体系的不断建构的呢?这将是本文接下来所要讨论的问题。——论文作者:周建新王梁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