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历史上的物理学教科书: 问题与方法
时间:
摘 要:文章对中国近代物理教科书发展的脉络和研究现状进行了初步梳理,提出一些可能的研究问题和方法。中国近代物理教科书发端于19世纪中后期,成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近代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与科学教育在中国的确立、汉语科学语言的形成、中国出版业的兴盛等方面密切相关。然而,现有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某些具体教科书的孤立考察,或从教育史和文化史方面浅显的讨论上。本文认为,关于近代物理教科书的形成、演变、使用及其影响,应该综合科学史、教育史、文化史等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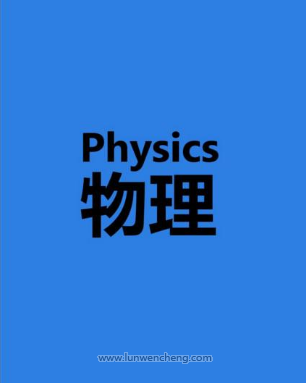
关键词:物理教科书 科学史 问题及方法
提起科学教科书,现代人大多不会陌生。从小学至大学,甚至研究生阶段,受教育的人们需用相当多的时间面对和钻研科学教科书。人们相信科学教科书所提供的知识,认为这些书是科学真理的化身,是学习知识、获得技能、通过考试乃至升学的重要依据和不二门径。然而,科学史界却持有不同的看法,认为科学教科书是科学共同体编写的用以培养新成员的载体,是已经发现的知识宝库,除少部分程度较高的教科书外,一般科学教科书不会载入富有争议的科学前沿问题。也正因此,长时间以来,科学教科书并不被科学史界所重视。[1] 然而,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一些西方科学史学者开始关注科学教科书,探讨其与科学教育、科学传播和国家教育政策等复杂的关系。相比较之下,近代中国科学教科书具有更为复杂的面向,发端于19世纪中后期,成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近代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同时,科学教科书与科学教育在中国的确立、汉语科学语言的形成、中国出版业的兴盛等方面密切相关。然而,长时间以来,中国科学史界对近代科学教科书的发展和变迁这一富有历史意义且影响深远的问题尚缺乏全面而深入的剖析。本文试图梳理近代物理学教科书的形成及演变的大体脉络,基于此提出一些可能的研究问题和方法。
一、为何研究物理学教科书
众所周知,自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物理学已发展成科学中最为重要的学科之一。也正因此,物理教科书在诸多门类科学教科书中颇具代表性。物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中叶,最初是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的。[2] 至20 世纪初,物理学已成为“自然科学之王”,揭示自然规律、探索宇宙奥秘最重要的学科之一。[3] 与此同时,随着科学内部学科的分化重组,物理学共同体的形成,物理学教育逐渐成为西方科学教育的重要部分。从一定意义上说,19世纪中叶的物理教科书正经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培养新生力量、传播科学知识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4] 实际上,物理学共同体的形成与物理教科书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日趋完善的物理学共同体催生了新式物理教科书,使其向着共同体所期望的方向演进。另一方面,逐渐成型的物理教科书则为共同体塑造了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才。
然而,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内忧外患。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非大力培养人才、积极学习西方文化而无以求存图强。在西方文化中,西方科学技术最具吸引力。而在西方科技中,多认为物理学最为关键。1862年,清廷开办京师同文馆。1869年,丁韪良擢升为同文馆总教习,在其推动下,格物学(即物理)成为正式课程。1888 年,同文馆增设格物馆,专设格物一席。据《光绪二十四年同文馆提名录》记载,增设此馆的理由是: “察格致一门,为新学之至要,富国强兵,无不资之以著成效,总教习于稽察各馆功课之暇,向以此学教官生,旋于光绪十四年,因馆课日繁,申请堂宪专设格物一席,以英文教习欧礼斐充补,俾广其传, 以启后进。[5] 引文的“格致”即泛指科学,而 “格物”则特指物理。为此,丁韪良等还专门编纂了中文物理教科书《格物入门》,之后又在此基础上编成《格物测算》。此后,一些教会学校也积极开设物理课程,编写了一些颇具影响的物理教科书。可惜,当时社会风气闭塞保守,国人虚骄自大的心态犹未消泯,以致包括物理在内的科学教育事业一向不为社会所重视,其收效也不大。[6] 甲午战败之后,国人开始觉悟,日本之强大是其善于学习西洋科学所致。故此,包括物理学在内的科学教育逐渐受到晚清朝廷的重视。20世纪初,废科举,兴学堂,推行新学制等一系列改革举措,物理课程成为新式学校教育的重要部分。严复在20世纪初即发表“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一文,提出“物理科学一事,不独于吾国为变化士民心习所不可无,抑且为富强本计所必需。”[7] 其主旨就是希望清政府加强以物理为首的科学教育。可见,物理学在当时士大夫心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
清末民初,随着物理教科书的翻译和引进,其在物理学知识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在一些官办学校中,由于缺乏精通物理的教员,大多学生只是根据教科书的内容学习物理。一般情况是,教师在讲台上读教科书,学生在下面附和。也正因此,评价物理教科书以字数是否合适为一个重要标准。有些教科书甚至直言每堂课念多少字为宜。因此,早期的物理教科书承载了主要的物理教育功能。另一方面,在学校外,物理教科书作为科普读物也颇为盛行。一些心向西学的有志之士纷纷购买此类书学习西方物理知识。比如钱钟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在其“自我检讨书”中就交待:由于条件所限,无法接受正式西方科学教育,为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他利用《国粹学报》征文所得二十元奖金购买了饭盛挺造所著《物理学》自学,后来自发组织理科研究会,聘请教师,购买物理仪器和设备进行自学。当时他们用的是日文原本,中文译本还未出版。为给其他学生提供方便,钱先生还主动翻译此书。[8] 由此可见,物理教科书在当时物理学知识传入中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近代中国,物理教科书经历了早期的口译笔述、后来的译自日本、以及直接英译等发展过程,经过多次学制变迁和教育改革,最终在民国中期基本定型。为推行科学教育,一些教会学校编译了多种科学教科书。据不完全统计,早期物理教科书有40 余种,其中大多通过西方人口授、中国人笔述的方式编译而成。从现代的角度看,这些教科书尽管存在不足或限制,但它们开中国物理教科书之先河,为此后物理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甲午战后,随着大量中国人留学日本,大多日本科学教科书被译成中文。王有朋先生编辑的《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收录了现存的1900至1910年间译自日本的物理教科书有近20种,[9] 几乎涵盖了当时日本出版的几乎所有的物理学教科书。这些书在国内颇为流行,一方面供新型学堂使用,另一方面是社会普通读者学习物理的主要门径。日译物理教科书无论在名词术语、表述语言以及知识结构等方面远胜之前口译笔述教科书,揭开了中国新式教科书的新篇章。随着国人精通英语的人日渐增多,一些西方的物理教科书被直接译成中文。然而,真正使中文物理教科书成型还是自编教科书。自编教科书相对比较复杂,可以说各个时期都有,且自编程度不一。比如在自强运动时期,传教士口译笔述的教科书大多是编译而非直接翻译,这些书大多基于多种底本译成。1895年后,一些留日学生在翻译日本教科书之余,也自编了一些书,这些大多是基于几种日本教科书东拼西凑的。民国时期,随着精通英语的国内科技人才的增多,自编教科书日趋成熟,且逐步顺应国内教育。
总之,物理教科书起始于晚晴衰落之时,兴盛于清民鼎革之际,历经口译笔述、译自日本、直接译自英美以及自编等阶段而最终定型。近代物理教科书在西方物理学知识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换句话说,缺少了对物理教科书史考察的近现代物理学史是不完善的。然而,物理教科书并非仅有一个单一、孤立的面向,其发展演变与多方面息息相关。作为传播物理学知识的主要载体,近代物理学的演进势必影响物理教科书的知识结构。另外,物理学名词术语以及物理书面语等表述形式也经历了颇为复杂的演变历程。作为书的一个门类,物理教科书的发展受到出版、印刷等方面的影响。
二、研究现状
长时间以来,对科学教科书的忽略不仅出现在中国科学史界,西方科学史界亦如此。过去,西方科学史界一般认为科学教科书只是科学知识的资料库,在科学史研究领域处于较低的地位。([1], pp.83-87)不过,最近十多年,西方科学史家越发认识到科学教科书的历史意义,开始聚焦科学教科书,从较为广阔的视角提出问题并开展研究。然而,中文物理教科书的相关研究还很欠缺。
物理学史方面,王冰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明清时期(1610-1910)物理学译著书目考》(1986)中专列“物理教科书目”一节,介绍物理教科书的内容以及出版情况。[10] 很多书,尤其是 20世纪初出版的教科书,作者大都没有提到。另外,此文对教科书和其他书的分类存在问题,一些当归为教科书的却归入了“专著”系列。戴念祖先生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学卷》仅用很少的篇幅讨论了“物理学书籍的翻译”和“近代物理学教育”,其中仅对较有影响的一些物理教科书进行了简单介绍,对这些书的成书过程及其影响鲜有涉及。 [11]
近年来,几位科学史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对清末一些物理学教科书进行了专门研究。以下为几篇较具代表性的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聂馥玲的博士论文《晚清科学译著《重学》的翻译与传播》对《重学》的翻译与传播进行了研究。[12] 清华大学李嫣的硕士论文《清末电磁学译著《电学》研究》对傅兰雅翻译的《电学》进行了讨论。[13] 还有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以傅兰雅翻译的《光学》、《声学》译著进行了专门研究。[14] 另外,有些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对较晚近的物理教科书进行了讨论。如咏梅的硕士论文《饭盛挺造《物理学》中译本研究》、高俊梅的硕士论文《晚清译著《力学课编》研究》[15] 等。以上这些研究大多对译本和底本进行了对比,讨论了译书的成书背景,对译介的物理学知识进行了分析,分析了物理学名词的发展演变等。这些研究多集中在物理教科书形成的早期,研究较为零散,只是对所关注教科书的发展情况进行简单的梳理,对整个物理教科书的发展演变缺乏关注。
科学教科书是科学教育的关键环节,如上文所述,这些书在早期承载着主要的教育任务。但实际上,近年来出版的科学教育论著,主要关注于科学教育的外在因素,探讨与科学教育相关的重要事件和近代教育界重要人物的科学教育思想,并未涉及科学教育本身,有关科学教科书的讨论更是寥寥。如曲铁华和李娟所著《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史》就是如此。[16] 孙宏安著《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史》虽然涉及一些物理学教育问题,但对早期物理教科书的演变的讨论远远不足。[17] 相比较之下,一些专论中日教育关系的论著对译自日本的科学教科书的讨论更为详明。众所周知,甲午战后,师日浪潮兴起。一方面,20世纪初,中国的留日学生从日本翻译了大量书籍,其中有很多物理教科书;另一方面,中国聘请了大量日本教习,任职于新式官办学堂。这些对物理教育发展都起了深远影响。日本学者实腾惠秀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18] 和汪向荣锁住《日本教习》[19] 分别从以上两方面对近代科学教科书翻译的始末有详细的讨论,其中设计很多物理教科书编译、印刷、使用的重要环节,对近代物理教科书的研究颇具参考价值。
近年来,教科书的文化意义逐渐引起学者关注,几种专论教科书文化的论著也相继问世。比如王建军的《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20] 分“清末教科书的传入”、“清末的自编教科书”和“民国初期的自编教科书”三个专题进行了讨论,讨论了清末至新文化运动时期国语教科书的产生和演变过程。汪家熔撰写的《民族魂——教科书变迁》一书从出版史的角度探讨了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发展状况。汪先生早年从事印刷业,长期服务于商务印书馆,熟悉图书目录学,尤其精于钻研近代图书出版。作者并不满足于一般书史的简略叙述,而坚持“研究出版史,必须见到书”的治学原则,所得结论大多比较新颖。石鸥编著的《百年中国教科书论》对近代教科书的发展演变作了简单的阐述。[21] 2010年,毕苑所著《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文化转型》一书, [22] 从近代教科书的诞生和发展对近代中国人“建造常识”的影响这一角度入手,探讨了教科书发展与近代文化转型的关系,试图发掘教科书所展现的中国近代文化的内涵。
不过,上述有关教科书的研究论著主要关注国文教科书,对理科教科书的情况很少涉及,相关的表述中也不乏错误。比如汪家熔的《民族魂——教科书变迁》第一章在谈及“益智书会”编辑的教科书时,说“如《眼科指蒙》、《天文揭要》、《百鸟图说》等都是普通随便看看的书,谈不上学校教科书”,甚至说“他们自己办的学校也不用”。而下此结论的根据是援引自顾长生《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一书中有关狄考文的一段论述“请一位刚刚入教的穷书生张干臣教识字启蒙,读《三字经》等”。 言下之意,登州文会馆的学生依然用传统的课本《三字经》,而其编著的《天文揭要》则不曾用作教科书。这其实是对文会馆课程及教科书使用情况不了解。实际上,《天文揭要》由美国传教士赫士和周文源根据路密司(Elias Loomis)的《天文学基础》(A Treatise on Astronomy)编译而成,于1891年出版。登州文会馆分备斋和正斎两级,备斋三年,相当于蒙学程度,主要包括国学经典,算术,以及一些宗教课程。备斋六年,开设一些理化课程。按赫士所序,文会馆是先以《天文学基础》为教科书,后将其译成中文。据傅兰雅在《中国教育指南》中的统计,《天文揭要》在出版后颇受教会学校欢迎,多所学校以此书为标准教科书。[23]
总的看来,以上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关于近代物理学史的研究。由于物理教育在近代物理学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故此近代物理学史研究者也多会论及相关的教科书。但现有的这些研究还远远不足,甚至连教科书的分类还存在问题。近年来,虽有一些学位论文以某些具体物理教科书为案例进行了分析,但这些研究仅限于对译本和底本的考证,译者的生平经历的介绍,以及科技术语的创制等方面,缺乏对近代物理学教科书演变历史的整体考察。第二,关于科学教育史的研究,偏向于科学教育的外部事件,这些研究对科学教科书讨论非常简略。第三,关于教科书文化意义的研究,近年来颇受教育史界所重视,涌现了很多文章和相应的专著。但这些研究多关注国文或历史等文科教科书,对理科教科书虽有提及,但非常有限,且有错误。
三、问题和方法
本文认为,关于近代物理教科书的形成、演变、使用及影响的考察,不应局限于科学史、教育史、文化史等条框,而应该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综合研究。
相关知识推荐阅读:要发表物理理论的文章如何选择期刊
首先,物理教科书是近代物理学知识传入中国的主要载体,其所承载的科学知识的传播、科学观念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关于这方面,可以提出一些有意思的问题。比如:近代物理学知识是如何通过中文物理教科书建构的?不同阶段的教科书所载物理学知识的结构有何不同?是什么因素导致中文物理教科书所载物理知识的结构发生了演变。总的看来,影响物理教科书知识结构变化的因素大体为三种:物理学本身的变化;教育政策的变迁;科学共同体的产生。
第一、物理学本身的演变。19、20世纪之交,物理学理论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物理学知识和理论上的变化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在中等物理教科书中。以美国传教士赫士译编的《光学揭要》为例,此书首版于1894年出版,第2版于1898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时隔四年,第二版《揭要》附录部分增加了“然根光”一节。所谓“然根光”,指的是X射线,具有非常强的穿透力,是由德国物理学家伦琴(Wilhelm Conrad Röntgen)于1895年发现,为了表明这是一种新的射线,伦琴采用表示未知数的X为其命名,“然根”是伦琴的音译。《揭要》第 2版用五、六页的篇幅分别阐述了“然根光之有无”、产生然根光的“虚无筒”,以及“然根光之用”。[24] 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的变化即如此,不同书所载知识结构的变化更可想见。
第二、教育政策的变化。中国近代经历多次教育变革。陈宝泉先生认为,1927年前,中国近代学制变迁经历了五个阶段,分别是:无系统的教育时期、钦定学堂章程时期、奏定学堂章程时期、民国新学制颁布时期和学校系统改革案颁布时期,[25] 早期的学堂章程一般都规定教科书的知识结构,而这俨然成了编写教科书的指南,尽管有些教科书并未完全按照学部或教育部等官方规定编书,但大部分书是基本是遵照规定编订的。纵观不同的章程和学制,可以发现知识结构的不同,而这种变化当然也就体现在了教科书中。
第三、科学共同体的形成。教科书与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西方科学史界关注的焦点,这方面研究的经典名著就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所关注的主要是西方科学共同体和教科书的互动。然而,中国近代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科学教科书是在科学共同体形成之后或过程中而自发形成的。而中国只是科学的传入国,一般认为,中国的科学共同体自1920年才逐渐形成。[26] 从最初的中国科学社、科学名词审查会到后来的中国物理学会,这些都是中国物理学共同体形成的标志。也正因此,科学教科书与中国科学共同体的形成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一方面,物理学教科书的推广和使用为培养新式人才、形成科学共同体起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逐渐形成的科学共同体对物理教科书的最终定型起了决定作用。以上这两方面的关系或可成为物理教科书研究的突破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