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重庆霍乱疫情应对与控制模式初探——以 1939 年、1945 年霍乱为例
时间:
摘要:1939年、1945年四川省爆发了两次大规模霍乱,全川大受影响。重庆作为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亦受到霍乱的严重袭击。霍乱在重庆爆发的原因,与日军1939年对重庆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密切相关。日军陆空立体式的作战模式,以及无差别轰炸,造成重庆难民数量的急剧增加,人口的流动为大规模霍乱爆发提供了外部条件。1945年疫情较1939年影响更大,卫生观念模糊、防疫知识匮乏成为该年霍乱传播主因。重庆霍乱模式是战争行为的衍生物,抗战时期重庆霍乱疫情的解决方式大致是“战争-疫情-应对-卫生观念”,即从外在问题到近代卫生观念模式,并且以现代卫生观念的官方普及行为为最终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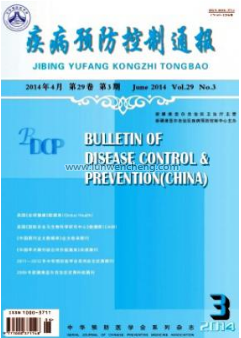
关键词:霍乱;战争;迷信;卫生
高传染和高死亡的特性让霍乱吸引了医史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共同关注。在历史学界,对霍乱的关注主要来自于疾病社会医疗史领域和历史地视阈下,特别是疾病社会医疗史领域内。余云岫先生在《霍乱沿革说略》[1]中对霍乱之来源、区分方法等问题作了介绍,为后世对霍乱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程恺礼女士的《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2]747-795的一文中对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霍乱起源地的问题进行再次梳理并提出环境变化可以影响病菌变化的观点;李玉尚先生《霍乱在中国的流行(1817-1921)》[3]在嘉道霍乱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1817-1921年的霍乱进行了研究与说明。此外,余新忠先生在《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4]对1932年的全国性霍乱有专门章节论述。在民国时期四川地区传染病研究薄弱的现状下,尚无专著探讨四川地区的霍乱。仅有的几篇论文中涉及的霍乱问题也十分有限,可以说民国时期川省的霍乱探究是疾病史研究上的一个薄弱环节。1939年、1945年的川省霍乱在传染病领域具有特殊性,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受到两次霍乱波及,具备较好的研究价值。本文拟从两次大霍乱入手,探讨特殊背景下重庆霍乱的应对模式。
一、1939年和1945年川省霍乱的传播
霍乱是对四川地区影响较大的烈性传染病。1939年和1945年的两次霍乱是民国时期四川地区较为典型的两次疫情,它们对川省造成了严峻的社会后果。由于死亡人数多、传播面积广等原因使得这两次霍乱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有关它们的传播情形,除与四川地区本身的环境条件密切相关外,还有其他因素亦影响了疫情扩散与传播。
《四川省志·卫生志》载,1939年川省霍乱,始自重庆难民。自抗战以来,难民涌入重庆的情况屡见不鲜,抗战爆发前夕,市区面积不到100平方公里,人口不到30万,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军政机构、工商企业、文化教育单位和络绎不绝的难民纷纷迁渝,外来人口急剧增加。到1937年底,重庆市人口已增至47万余人,并开始拥入大量人口。从1939年2月起,为躲避日机轰炸,部分市区机关、学校和商店开始向重庆周围地区撤迁。[5]200-201这些难民成分较为复杂,从社会救济角度来看,他们实际上包括从敌占区逃出的流民,也包括其他遭受自然灾害部分地区的难民。相较于和平时期,战争时期的难民所包含的范围无疑更大。“灾民是瘟疫的易感人群”,夏明方在《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一书中指出民国时期的人口迁移具有临时性、季节性等迁移的特点,且回返率高,永久性的迁徙少。川省民众自古以来的盆地意识也制约着难民迁移的距离和地域范围。1939年4月底伴随着侵华日军陆空的联合袭击,霍乱开始在重庆蔓延,并于6月向西传入自贡,盐工首当其冲地成为这次霍乱病的高发人群,夏季为霍乱的高发季节,盐工群体人员密集,且处于高温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疫情传播极快。自贡在这次霍乱疫情中受到重创。据统计,1939年就死亡约5000人[6]141,然而疫情之势并没有停止,继续北上。7月,霍乱疫情传播波及川北一带,成都、德阳、郫县等地均受影响,据四川省档案馆档案记载,民国廿八年(1939年)仅德阳一地就有7787人感染霍乱[7]。8月,疫情经乐山、洪雅至雅安等西康地区,全省数十县受灾。
民国重庆霍乱疫情应对与控制模式初探——以 1939 年、1945 年霍乱为例相关期刊推荐:《疾病预防控制通报》创刊于1986年,由新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办。是中华预防医学会系列杂志优秀期刊,1992年被评为全国基础医学寄生虫学核心期刊。主要报道鼠疫、布鲁氏菌病、克山病、大骨节病、碘缺乏病、氟(砷)中毒病、包虫病、黑热病、血吸虫病、疟疾、肠道寄生虫病、性病/艾滋病、结核病、职业卫生与职业病、计划免疫、放射卫生与放射病、消毒杀虫灭鼠、医学动物与昆虫、健康教育、社区卫生、农村卫生、妇幼保健、卫生监督等疾病预防与控制研究的相关内容。
1945年川省霍乱的严重程度,为民国时期该地区疫情之最。笔者查阅档案资料,统计该年霍乱患者为15951人。相较其他年份可以看出,1945年川省霍乱在患病人数上达到了民国时期该地区的顶峰。《霍乱紧急报告第一号》记载,本年2月泸县、内江发现霍乱可疑病例,但因未经检验证实,故未发表公报。该年川省首例确诊的真性霍乱于6月3日发现,患者为巴县白市驿居民。后在重庆地区逐步蔓延,新开市、渝市、北碚等地相继出现霍乱疫情报告,商、军等行业人员有所涉及,另有从外省迁移之人员。[8]重庆霍乱之势发展迅速,整个川东地区相继出现霍乱病症。六月间,成都、合江、大竹、叙永等31个县相继出现霍乱,蓉市从6月24日发现真性霍乱以来,到7月21日止,经查明共死257人;合江则在霍乱爆发后由于医药缺乏,平均每日死亡达15至16人。[9]在这样的情形下,霍乱又呈现出北上态势,广元等川北地区亦未逃过此劫。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霍乱波及川省六十余县,较之1939年霍乱影响面积更大。
两次霍乱的传播范围之广,患病人数之多远远超过民国其他时期。笔者统计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年(1927年)至建国前(1948年)霍乱的地理分布及患病人数。其中1945年川省霍乱波及地区多达66个,1939年涉及23个地区,其余年份除1938年(10个)外,均不超过10个地区;这两年的疫情几乎囊括川省东、中、北部大部分区域,患病人数也是有统计年份中最多的两年。大规模的传播和传染,与交通有直接关联。1945年川东、川北的霍乱就是一例,“成渝路上的内江,本月中旬就已发现真性霍乱,现在已沿成渝公路传至资中、内江等县,死亡聚众……川北的乐至等县,也已发现霍乱”。[10]1939年全国遭遇的气候异常成为霍乱猖獗的另一大诱因,“因气候干燥异常……中国西南霍乱及脑膜炎颇为猖獗,威胁该区全部居民”。[11]川省霍乱之传播具有密集性的特点,霍乱爆发地区基本成片状分布,零星分布的地区很少,发病时间亦多集中于夏季,与旱灾发生的时间相吻合;瘟疫波及的地区正是川省人口密集之区,大量的人口成为霍乱疾病繁衍的重要载体,人口流动带动疾病流动,霍乱开始蔓延。
重庆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成为两次霍乱疫情蔓延最早或较早的地区;另一方面,重庆在民国时期曾多次发生霍乱疫情。笔者对1927-1948年间川省出现霍乱的次数进行了统计(见表1),发现重庆有九年均出现了霍乱病症,成为这一时段川省出现霍乱最多的地区。历次重庆霍乱的爆发原因、社会应对措施在每次疫情出现后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和处理方式,成为其有别于川省其他地区霍乱的特殊性。
二、大轰炸下的重庆霍乱与防疫观念初建
随着1938年底国民政府迁都的最终完成,重庆地区不可避免的成为日军的重要进攻目标。空袭成为日军立体化作战方式的重要手段。“对城市无差别轰炸却最终演化为规模空前的对重庆的抗战大后方的战略轰炸”。[12]321939年1月起,重庆开始遭受日军空袭。在受多雾天气的影响下2-4月被迫停止轰炸,5月起发动在华陆海军航空力量,进行了“100号作战”轰炸,这一轰炸是惨无人道的无差别轰炸任务,5-10月成为日军主要轰炸的时期,轰炸次数占本年总袭击次数的75%。[12]126相较之1938年的轰炸频度和轰炸后造成的损失,1939年日军对重庆的轰炸达到了一个高峰,霍乱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蔓延开来。
霍乱全年均可发生,多起病于夏秋季节,亚热带季风气候的重庆气候温暖湿润,5月的气温足以孕育霍乱病菌的滋生。大轰炸过后的重庆一片狼藉,环境污染严重,垃圾、老鼠、污水及粪便到处可见,市容卫生极差,“炸弹坑里的停滞的水孕育蚊虫,痢疾越来越厉害,霍乱、麻疹以及一种讨厌的味肠寄生虫亦然。”[13]267难民的大规模流动造成的疾病流动与人口流动一样无法得到控制,战火之中的防治工作困难重重。霍乱疫情在这样的条件下无法遏制,大批市民间接染病。“五·三”、“五·四”两次对重庆市区的狂炸后,重庆市就发生了严重霍乱;[14]3176月化龙桥一带发现霍乱,来势凶猛,当月死亡就已达200多人。[15]53原来的霍乱医院与病床的增加仍然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病人,“全市一百病床,实感不敷,本局霍乱医院床位早已告满,而南岸一带难民收容所霍乱病人尚有增无减,本局事业费内已无法匀支增设新院或扩充病床”。[16]民众在大轰炸下情绪不稳,治疗过程中不守规定,给治疗工作带来困难的情形屡有发生,如李子坝屠宰场内的霍乱医院就因家属不守院规发生纠纷而给疫情控制带来了一定难度。[17]
政府对重庆霍乱问题的解决是从卫生设施入手的。开始普设诊疗所,并组织清洁大队以及卫生保健等事宜。从8月开始,新的针对霍乱疫情的医院开始设立,与此同时进行的还有霍乱防疫注射。卫生局对防疫注射的对象和注射采取的形式均有相关安排,“该局在李子坝及南岸海棠溪分设霍乱医院两所,并另设分诊所六,同时开始霍乱针注射,凡机关通知该局后,即派医士至各该机关注射,市民即可自行前往各处诊疗所注射,该局并派医士至各贫民区挨户强制注射,此外并在各轮埠码头车站代旅客注射”,但对已入秋后是否可以完全防止霍乱仍不敢给确定态度,“惟依目前情形论似可扑灭矣”[18];组织清洁大队,负责洒扫街路,清除垃圾,收捕蝇鼠,整理防空洞,设立公共厕所;设立诊疗所虽是战时没有足够经费退而求其次之办法,但免费实施的态度和政府的反应无疑对霍乱控制有益。
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大轰炸的初始阶段,霍乱疫情扩散的初期政府并没有立即出台积极的应对措施,使得霍乱疫情蔓延甚速,但当政府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后(8月之后),战争下的霍乱便得到了一定的有效控制。笔者查阅1939年的相关霍乱资料,发现呈请类的档案占该年档案资料的多半数,当局政府对这些呈请基本上甚少回复,虽不排除由于保存问题而造成的档案缺失,却也甚少从其他著作报刊中看到对霍乱的救治,多数都是在对霍乱疫情进行报导,而非解决。即使已经意识到霍乱危害“较敌机盲目狂炸尤为惨烈”[19],但有关设立霍乱医院、派拨霍乱药品、维持霍乱医院秩序的呈请大多没有回复。1939年之后的大轰炸时期,虽然重庆依旧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当中,霍乱的应对却较前积极不少。这可能与霍乱初期政府和民众都全身心忙于应付轰炸而忽略对疾病的关注有关,引起注意后,霍乱是可以被防治的。
政府在相关部门的文件中,呼吁防疫注射的文件逐渐增多,“死者已有数人,请各位同胞速来敝队诊疗所注射霍乱预防针”;[20]“近日渝市霍乱流行,自宜预为防范该栈员工应从速注射防疫针,希即分别向附近卫生医所予以注射”。[21]能够积极防治霍乱的行动也越来越多,“高滩岩地方监狱大队宿管共有病人□名已死者2人,该队由北川开拔来渝(根据防疫周报所载目前汉中广元一带系疫区)当即督同技术人员用石灰及漂白粉等在病者住处一带先行消毒,将病人送往市立传染病医院医治,并取病者大便回局,经过细菌培养业已证实系属霍乱,正核办间奉”。[22]除卫生局和市政府外,军、工、商等部门也做出了应对措施,重庆市警察局“办理霍乱预防注射依照军医署印发霍乱防治实施办法,并对士兵饮食卫生加以管理,除分令外,遵照并饬属,遵照为要此令”。[23]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材料库“为职工二一万二十余人之身体健全起见,拟广扩注射伤寒及霍乱疫苗以资预防”;[24]兵工署“叠经本部严令各部队机关学校切实遵行,并另订新兵霍乱预防注射及拨收办法通饬施行后在案”。[25]“到19世纪末,政府对疾病预防事物介入认识的缺失,成为中华文明衰弱的有力象征”。[26]79南京国民政府似乎在此时更为深刻地意识到霍乱与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胜利之间的联系,后期的防治之路似乎较之前慢慢向前。
除政府部门外,社会各界人士也在关注霍乱并给予一定的帮助。以豫丰合计纱厂为例,该厂员工毛桂英因身染霍乱急需救治,纱厂承担起了毛桂英的救治义务,向霍乱医院致函,请求其收治染疫员工住院治疗并且承诺愿意承担该员工的治疗费用。[27]相比起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对霍乱的救助程度不如政府的实施力度大,但疫情来临时,依旧在防治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39年的重庆霍乱,大轰炸成为重庆地区不同于川省其他地区发生霍乱的动因,也为民国后期的霍乱防治敲响了警钟。战略轰炸在这一年由原来的小规模袭扰和试探性轰炸逐步扩大为无差别、较大规模的轰炸,尤其当日军轰炸任务集中于重庆市区及近郊之时,让政府和民众首次直面轰炸带给城市的损失和伤亡。仅五·三轰炸当天,“下半城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被炸成废墟,包括当时银行林立的金融区陕西街被炸得七零八落,商业繁盛地区的商业场、西大街和新丰街一带几乎全部炸光”。[12]127城市的基建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民众身心在战争中受到伤害,环境恶劣、轰炸频繁的特殊时期使霍乱有了可趁之机并开始蔓延。
如果说1939年作为大规模残酷轰炸开幕前实战演练的一年,那么它也成为霍乱疫情防治的探索之年。在这一年深层次的霍乱防治措施及疫情认识在政府和民众中被普及,重庆的防治工作在不断地认识与被认识中展开着,二十八年疫情仍属于探究阶段,在疫情应对上并非总是成熟和有效,但各种疫情控制手段却也在不断被应用和起作用。疫情的控制主要由政府组织进行,以建立疫情防治机构(诊疗所、霍乱医院等)、整顿环境卫生、注射防疫针等方式为主,当这些措施施行得力之时,疫情也得到了很好的防治。社会各界对霍乱疫情也进行着关注并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来施行霍乱救助。现代卫生理念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的防疫形式较为成功的应对了1939年的霍乱疫情,更重要的是,这一战争下的霍乱模式在以后的霍乱防治工作之中保留了其精髓,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1945年重庆霍乱疫情的特殊性与政府的应对
从疾病传染和观念接受史层面来看,1939年的霍乱是大轰炸下的特殊疫情,那么1945年的霍乱疫情救治,则进一步体现出社会救济与防治特点,随后的卫生观念普及则进一步凸显了官方角度的疾控进步。霍乱疫情的出现与社会应对,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其本身所蕴含语境的时代背景,成为卫生观念现代性植入的表现。
重庆自1939年霍乱后,至1945年之前再未出现过较大的霍乱疫情。1945年川省霍乱爆发后,重庆首当其冲。据不完全统计,仅重庆市郊就出现479例,重庆市区内霍乱蔓延更是常态,“渝市从霍乱传来自六月三日开始,立即蔓延全市。市民莫不谈虎色变,至六月中旬,疫情益见扩大,死亡约计数十起”。[28]仅仅一月时间,“全市因霍乱而死的死亡率,迄今无人能有统计,但棺材店确实生意大发,一口薄棺材,开口就是五万元”。[29]在霍乱猖獗的背后,是传统习俗与现代理念的矛盾,是霍乱患者带来的复杂性,他们共同构建了民国三十四年的霍乱模式。
(一)曲折发展中的霍乱控制模式
在政府的努力下,霍乱在逐步控制。这一年的霍乱出现在六月,然而五月时重庆地区就已对霍乱预防做出了反应,“查现时值夏令,气候亢热,种种流行性病□□散布蔓延,查本库为职工二一万二十余人之身体健全起见,拟广扩注射伤寒及霍乱疫苗以资预防。贵局遣派医师二人驾临本市代为注射”。[30]六月首例病例出现后,当局在较短时间内做出应对反应,政府各个部门开始对抑制霍乱蔓延采取手段,进行疫苗注射、建立霍乱医院和清洁卫生等防御措施。注射霍乱疫苗是最直接且相对有效的预防方式,关于注射的饬令和已注射的地区文献多有记载,“以歇台子等处发现类似霍乱患者,嘱派员前赴上开各地,施行注射,七月五日派员前往办理并已令饬第十一卫生所就近普遍为居民注射”。[31]“近日渝市霍乱流行,自宜预为防范该栈员工应从速注射防疫针,希即分别向附近卫生医所予以注射幸勿自误为要”。[21]霍乱医院也随着疫情的散播加以建立,“经会同防治霍乱委员会并发动民众团体于城区江北南岸迁区先后成立临时霍乱医院计十余所,除仁爱医院一部分霍乱病床收住院费外,其余均一律予以免费收治”。[32]卫生管理工作也在推行中,“本局会同防治霍乱委员会办理关于取缔路旁冷食摊贩、检查饮食商店、清除污水死鼠等,经与警察局密取联系,分别办理除向督促切实推行外,准函前后相应复请”。[33]这一时期的霍乱得到了一定的重视,防治手段开始频频出台。
此外,防疫知识的传播成为霍乱爆发之时的又一重要控制措施,在这一年大量的霍乱预防知识被普及和宣传。这些知识从霍乱疫苗的注射、饮用水消毒、生活环境的状态等方面入手进行霍乱预防的讲解。社会局报送救济院的霍乱预防办法中如是写道:“一、本院已向卫生局恰领霍乱菌苗,回所对员工普遍注射。二、饮水应切实消毒或备沙缸,并须煮沸后方可饮用。三、菜蔬类应严加检查并煮熟食用。四、禁止所生食水果及生冷类食物。五、令饬所生全体动员近日消减蚊蝇以防传染疾病。六、厨房及厕所应力求清洁,并常撒以石灰,如发生传染病时应速施救治或送医院诊疗所,同时专案院报备查。八、切实整饬环境。”[34]教育局亦多次颁布霍乱预防方法给各个学校,对学校预防霍乱和发生霍乱后采取的措施有明确规定:“在校学生应立即注射防疫针,并应切实注意环境卫生、饮水消毒及利用集会时间对防疫知识详加讲解,劝说学生不吃生冷,不食不洁之物。如有寄宿学生,即行分食所用碗筷,一律就餐前用沸水蒸煮,以杜传染,已在校内发生病症,立即隔离”。[35]诸如此类的霍乱预防内容还有很多,他们从现代卫生防疫角度切入,进行防疫知识的宣传,使重庆霍乱的解决方式以现代卫生医疗知识为主。政府采取强硬手段来进行霍乱疫情的调控,姑且不论这些防疫措施是否完全发挥成效或实施是否行之有效,至少现代的卫生理念已经开始普遍运用于防疫过程之中,用以对抗迷信和无知。
这一年社会各界依旧对霍乱的控制起到了一定的督促作用。六月霍乱蔓延至重庆之时,有人向警察局发出如是呈请:“近来本市霍乱流行,尤以沿江各码头患者甚多,其死亡率颇为惊人。(据此当地居民称,经朝天门一带,每日运过江掩埋之棺木最多者竟达百具,临门江码头最多时达八十余具),事关本市市民生命安全,拟请:一、函请卫生局派员调查设法防止(虽非真性霍乱亦应防止)二、令各分局注意霍乱蔓延之情形,随时具报并详确统计死亡数字,以供查收。”[36]社会人士对救治霍乱病症起到间接的促进作用,在他们的关注和呼吁下,政府可以更快了解疫情的蔓延情况和了解民众需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行为带有一定的监督性质,在疫情防治中扮演催化剂的角色。
然而,控制的步调因为一些并不有效的习俗而打断。民众面对霍乱时,时常会出现一些愚昧和落后的行为打乱霍乱工作的进行。[37]卫生知识的空白及破坏卫生工作的行为时常发生。有些地方缺乏公共设备,“炉灶分别炊烟弥漫,火星四散,余灰遍地,故随时有发生火警险。至于污水垃圾随地倾倒,瓜皮果核任意抛掷,蚊蝇腐集,臭气四溢,尤属妨碍公共卫生。”但“竟有少数不明事理之人纵容妇女或佣工任意破坏整个卫生秩序,能循序渐进,若以团体力量严刑禁止,结果难免遭受意外之侮辱,尚竟置不问,则公共福利永无建设之一日,不得已呈请”。[37]民众对卫生常识很为陌生,甚少了解,一些霍乱发生的地区,“天然环境欠佳,前彼复有公厕及渣堆之扰,附近居民流浴成性,素无卫生常识”。[38]对生活垃圾的处置也十分不当,“龙门浩境内近五日来患霍乱而死专达五十七人,但该卫生局迄未派员前往为居民作防疫注射,在龙门浩区垃圾污水遍及可见,炎阳之下,熏人欲倒”。[39]
此外,还存在市民忽视、排斥注射和以迷信巫术解决霍乱问题的行为。注射是当时最为行之有效的方式,然而“本市霍乱猖獗,蔓延甚速,若不急为医治,生命岌岌堪危,兹为防患未然计,自应预先注射防疫针,以免传染。但一般市民,每多忽视,意在观望,以致各处流行,时有死亡”。[40]排斥注射的情况亦时有出现,“歇台子、七牌坊、大坪箭道子、萧家湾新市场等各处居民及筑路工人时发现有类似霍乱病患者,为顾虑各该处居民健康而免传染蔓延计,曾派军医前往检查注射,但竟被拒绝”。[41]第六区在审查霍乱防治过程中,发现“市民多以红十字黏贴门首以期避免传染”[31]的行为。民众选择迷信巫术之法解决霍乱,诚然他们应对霍乱的手法并不高明,然而笔者仍不愿用愚昧无知来定义民众之做法,民众如何应对霍乱疫情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医药资源丰富与否、患病者自身的经济情况和信教情况等因素有关,面对迷信之法,有效解决的方式应当是现代卫生理念的传播和普及。
面对霍乱,这一年里政府依旧是疫情的主要控制者,其控制手段以现代卫生防疫之法为主,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和肯定。无论是政府亦或是大多数民众,都开始相信注射疫苗、清洁卫生等措施是控制疫情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然而作为新生事物的现代防疫之法,它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不少民众对防疫措施表现出了不信任或者不配合。在政府控制疫情的过程中,如何向民众普及新观念,间接地影响着霍乱疫情的控制。道路虽然曲折,但大量的防疫宣传和人员监督在努力扭转着这一局面,这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