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术谱系
时间:
摘要:本文从中西方比较的视角,探讨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术谱系特征,对中国政治地理学的未来发展路径进行了展望。本文认为,以西方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为背景,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可概括为萌芽期、停滞期和复兴期3个阶段;当前政治地理学在中国的研究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但仍具有离散的特征。总体而言,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主体包括探讨军事倡议、外交政策的“地缘政治学者”和地理学者中关注政治要素的“兼业政治地理学者”,这两者存在部分的交集;在中国政治地理学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张其昀、鲍觉民、李旭旦、张文奎、王恩涌等学者为首的几个谱系,但总体而言政治地理学在中国仍然主要受到外源性理论影响,学科的概念和方法体系仍不完善,在此背景下的研究共识形成、学术共同体和学科知识体系构建仍是今后亟待解决的课题。结合这一思路,本文提出了更为均衡的中国政治地理学发展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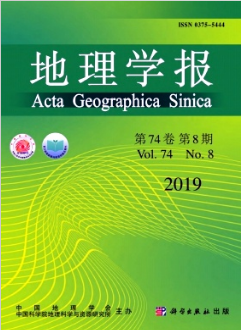
关键词:政治地理学;学术谱系;外源性;内生性;中国
1 引言
受中国地理学会委托,笔者于2012年起开始进行政治地理学发展谱系的整理,主要是对一些代表性学者的访谈,以及对相关研究成果的解读。同时,利用参加政治地理学相关学术会议的机会,向相关学者求证求教,对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渐次总结。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对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术谱系进行归纳,以期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提供指引。国内目前对政治地理学理论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但相关的研究仍比较零散,本文期望对这一学科共识的形成有所贡献。
本文首先在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大背景下,概括西方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轨迹,以此作为后续分析的基础;继而,梳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脉络、发展阶段和谱系;在此基础上梳理不同阶段的重要学者及其派系传承,进一步明晰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特征;最后,在中西方比较的基础上,讨论中国政治地理学未来发展的路径,并提出相关建议。
2 西方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脉络
在西方,政治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主要研究政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世界认知与空间权力[1-5] 。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 于1897年出版了《政治地理学》一书,标志着政治地理学作为现代人文地理学科的重要分支学科正式创立[1] 。自此,西方政治地理学正式走入地理学大家庭。现在回看,迄今为止的西方政治地理学发展大致可归纳为以下3个阶段。
2.1 古典地缘政治学兴盛时期
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拉采尔一生致力于“生存空间”的研究,他认为领土扩张是国家获取生存空间的唯一途径。受其影响,其后的政治地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地理特征和国家间关系的分析,为国家领土扩张服务。其中,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 (Halford Mackinder) 成为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者。他在其著名的 《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一文中,从英国维护霸权的需要,提出了心脏地带概念[1] 。此后,相关的研究开始盛行,政治地理学因其实用的治国之道而逐渐为人熟知。许多地理学家如美国的艾赛亚·鲍曼 (Isaiah Bowman)、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德国的卡尔·豪斯霍费尔 (Karl Haushofer),均以地理学家的身份对其所在国家的外交军事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拉采尔的影响下,瑞典政治学家约翰·鲁道夫·契伦 (Johan Rudolf Kjellen) 创造了“地缘政治学”一词,并成为后世广泛运用的核心词汇。尤其是德国的豪斯霍费尔,发展了众所周知的德国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为纳粹德国的侵略战争提供理论支撑,更使“地缘政治”一词广为人知并几乎成为政治地理学的代名词[6] 。因为在国策制定方面的“贡献”,地缘政治学 (政治地理学)曾经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但也因为对纳粹国策制定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其声誉一落千丈[6] 。
2.2 政治地理学的“去政治化”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20年左右的停滞期[7-9] 。20世纪70 年代后,政治地理学在西方复兴,但是其研究内容、方法和范式都发生了变化。伴随着对地缘政治与战争之间关系的反思,政治地理学开始“去政治化”。一些相关的面向政策的传统地缘政治研究转移到了国际关系等地理学之外的领域,如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和基辛格 (Henry Alfred Kissinger) 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外交和地缘倡议的著作。另一方面,一些政治地理学者把他们的研究兴趣扩展到国家内部的对象上,开始关注“政治性”较弱的一些领域。如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籍着“计量革命”思潮,开始关注选举地理等相对依靠定量分析而又“无害”的议题[10-12] ;20世纪90年代,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13] ,一些政治地理学者提出批判地缘政治学(critical geopolitics)[14-15] ,对主流地缘政治思想进行解构和批判性反思,剖析隐藏在话语和地理知识等背后的权力关系等[16-18] 。
2.3 政治地理的“多尺度化”时期
1982年国际地理学联合会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 IGU) 设立了政治地理研究小组,同时《政治地理学季刊》(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正式创刊,标志着西方新政治地理学 (New Political Geography) 的确立[5] 。新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内容超越了古典地缘政治,研究对象也从“国家中心主义”扩展到多尺度空间[7-9] 。20世纪80年代,皮特·泰勒 (Peter J. Taylor) 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世界体系理论[19] 引入政治地理学,为政治地理学的多尺度分析提供了整合框架。这一时期西方政治地理学关注的主题逐渐拓展到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权威弱化、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内战纷争、新帝国主义、霸权、信息的政治空间、地理知识的生产、政治制度、政治景观和表征的权力等[20-25] 。此外,地方政治的研究也开始兴起,并被联系到不同层次的权力关系进行复合分析,如从水平的 (在不同的地区间) 和垂直的 (在不同的尺度间)角度对冲突进行研究[26-28] ,等。如今,“国家”仍是西方政治地理学关注的基本单元,但已不再是唯一的研究对象,“条条大路通罗马”,多尺度和跨尺度的研究已成为当今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新范式。
2.4 小结
以上西方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到3条脉络:① 是根植于拉采尔和麦金德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古典地缘政治学,这个分支主要服务于军事和外交政策的制定;② 是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建立在批判理论之上的新政治地理学。这个分支产生于对第一个分支的批判性反思中,以约翰·阿格纽 (John Agnew)、约翰·奥劳夫林 (John O'Loughlin) 等为代表;③ 主要关注多尺度政治,并且常与其他学科如城市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交织在一起,代表性学者如泰勒、罗恩·约翰斯顿 (Ron Johnston)、多琳·梅西(Doreen Massey)等。如泰勒除了提出政治地理学的多尺度框架外,还提出世界城市网络等城市地理学理论;约翰斯顿不仅是选举地理学的知名学者,也同时活跃在社会地理学领域;梅西同时也是经济地理学和女性地理学领域的杰出学者。
基于以上对西方政治地理学发展历程的梳理,也可以发现3个特征:
第一,学科范式的转型。在理论上,西方政治地理学从古典地缘政治偏重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逐渐走向后现代批判理论的多元声音;在方法论上,西方政治地理学经历了从区域分析向世界体系分析的视角转换;在研究对象上,以国家为基本单元,但已从国家间关系的单一尺度分析扩展到包括全球、超国家区域、城市、社区和个人等多尺度、跨尺度的综合分析。
第二,学科理论的演进。与第一点相关,西方政治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也是不断变化的,古典地缘政治学主要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泰勒的多尺度分析主要是受到沃勒斯特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批判地缘政治研究主要是受到福柯等后现代哲学思潮的重要影响。
第三,政策科学的基因。西方政治地理学始终是“入世”的,在积极回应发展需求和现实政治。如古典地缘政治理论的兴起主要呼应英国遏制俄罗斯为主的陆权和德国打破“一战”后地缘格局等国家需求;选举地理和地方政治的分析主要满足和平时期国内不同利益主体的需求;近年来兴起的对恐怖主义的研究则主要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极端势力带来的挑战等。即便是“批判地缘政治”,实际上仍然浸透着“为国服务”的思想。 “批判”实际上也是为了避免国家的错误决策,因此其服务的是广义上的国家(不一定是当任政府),这一逻辑在福柯关于新自由主义治理的论述中有非常精彩的解释[16-18] 。
3 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脉络
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与中国地理学的整体类似,存在内生和外生的“二元结构”[29] 。前者具有历史积淀和较强的实用导向,但是缺乏严谨的理论归纳;后者主要是新兴的学说,理论性较强但本土化程度较低。此外,类似于西方政治地理学的“隐性化”发展,中国也有一些“事实上的(de-facto)”政治地理研究在不断增长。
3.1 内生的政治地理思想传承
内生的政治地理思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比如战国时期倡议家苏秦和张仪为秦国提出辩证但相反的一对地缘政治外交策略:苏秦强调将秦国作为支点的纵向 (南北) 联盟 (合纵),张仪则提出了一个横向 (东西向) 联盟 (连横)。几乎在同一时期,范睢提出另一个军事外交倡议,建议与较远的国家结盟而攻击较近的国家(远交近攻)。同样,诸葛亮提出的“隆中对”作为一个详细的地缘倡议帮助刘备建立了蜀国,等。长期以来,类似的外交—军事思想一直被视为重要的“中国智慧”,在当代中国仍被时常提起。不过,这方面研究较少被整理,多体现在古代文人的梳理思辨[30] 和部分历史地理研究中[31] 。直到最近,政治地理学者才开始重视这一领域的研究[32] 。
内生的政治地理思想在近现代中国也有体现。比如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倡议现在仍用于非洲和中东的一些冲突地区,有学者甚至认为最近美国的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 在总统竞选中也运用了这一倡议[33] ;此外,如毛泽东提出的 “三个世界”划分,邓小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 来处理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他们都可以视为内生政治地理思想的践行者。这些思想大都是基于中国的传统哲学如易学(易经),这有点类似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所起到的作用。这些思想属于实践层面的创造,但尚未衍生更多学术上的思辨和讨论。
3.2 外生的西方地缘政治学的传播与实践
当前在中国被用于教学和研究的政治地理学体系主要是从西方学术界引进的外源性研究范式,而不是基于前述的内生性思想。王恩涌先生认为,西方政治地理学的引进始于20世纪初。沙学浚在他的《国防地理和政治地理》中,第一个运用地缘政治的概念从地理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国防政策[34] 。同一时期,中国学者翻译和引进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和其他的欧洲经典地缘政治学说[35-38] 。在此基础上,也出现了一些探讨地理形势如何影响国家政策的实证研究[34] 。这些成果的作者是中国第一代政治地理学者[34, 39] 。他们聚焦于地缘政治,致力于地理环境/背景和国家政策之间关系的研究。由于缺乏连贯的研究范式和系统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成果现在看起来都是比较初步和零散的,但他们在推进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尤其是西方地缘政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上,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20世纪50年代后,受西方地缘政治批判和新中国学科发展偏好的影响,政治地理学在中国也被视为伪科学,发展全面停滞。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大约30年,直到20世纪80 年代人文地理学科建设被重新提上日程[31] 。1978年改革开放后,许多地理学家的呼吁促成了政治地理学复兴[34] 。如 1984 年李旭旦建议在 《中国大百科全书:人文地理学卷》中,加入“政治地理学”词条;鲍觉民在其文章《政治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和《再论政治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中,讨论了中国发展政治地理学的重要性[39] ;张文奎在教材《人文地理学概论》中,专门用一章讨论了政治地理的性质、研究对象和内容[38] 。他们的努力无疑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地理学重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政治地理学的复兴,更多学者开始对政治地理问题产生了兴趣,相关的研究开始起步。如周介铭提出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框架,包括中国的领土配置和行政单位、世界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中国外交的发展策略等[40] ;张文奎等在介绍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地理学发展状况的同时,对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总结,并详述了世界政治地图的形成和演化[38] 。此外还有王国梁[35] 、王正毅[36] 、肖星[37] 、沈伟烈[41] 等,都是这一代学者的代表。这些学者在推动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组织和学科体系形成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大多隶属于各大高校,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开始了外源性科学的本土化升级,人文地理学也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这本可以是中国政治地理学的一个发展契机,去整合本土的实证研究与外源性理论,就像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旅游地理学在这期间所做的。但是,这种整合并未发生。由于政治地理学的本土化需求未被激发,之后的中国政治地理学成果多表现为之前的惯性延续,即对西方已有地缘政治理论的解读,其中多数是对外来作品的翻译[41-46] 。这一时期政治地理学的教学研究相对活跃的机构包括北京大学、国防大学等,这些大学主要考虑的是国家军事/国防从业者的培训。
进入21世纪,更多的西方地缘政治学研究成果被介绍到中国,比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等学者的相关著述。此外,除了对西方成果的引入外,应用西方理论对中国案例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也多起来。这些研究的主题包括冷战后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47] 、海洋地缘政治[48] 、资源与流动的政治[49-50] 以及地缘倡议[51-53] 等。这些研究仍然主要是基于西方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和概念。同时,相关的学术讨论也呈逐渐增多的趋势,但这些讨论不全是由地理学者主导。
《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术谱系》来源:《地理学报》2018年12期,作者:刘云刚; 安宁; 王丰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