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的戏曲理论
时间:
摘要:杨维桢是元代末年诗坛上的领军作家,在诗作上开创了“铁崖体”,他对元代新产生的曲也较为关注,在一些曲集的序跋中,对曲的渊源、艺术形式、内容等有关戏曲创作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为一位具有诗人身份的曲论家,他的戏曲理论在元代曲论中,也自具特色。
关键词:戏曲艺术;杨维桢;艺术理论;序跋;今乐府;情性;讽谏;中国传统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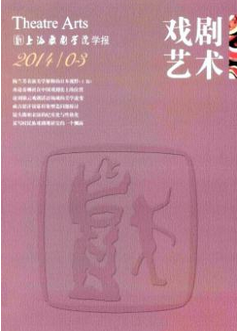
杨维桢是元代末年诗坛上的领军作家,以“铁崖体”著称于时。对于元代新产生且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的曲,杨维桢虽所作甚少,现仅有小令、散套各一,但他对曲的创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为一位具有诗人身份的曲论家,他的曲论在元代的曲论中,也自具特色。
一
、杨维桢的生平与曲作序跋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铁雅、东维子、铁笛道人等,诸暨(今属浙江)人。少时颖悟好学,日记书数千言,其父甚重之,特延师教之,并在县北五十里的铁崖山上筑楼,楼上置书万卷,恐其怠惰分心,撤去楼梯,以辘轳传食,在楼上苦读,五年不下楼。经史百氏,无不淹通。弱冠,又命其外出游学。
元泰定四年(1327)进士及第,任天台县尹,在任上严惩恶吏,并因此得罪其党,被免职。后任钱清场盐司令,深感盐赋病民,屡次上书,请求减轻盐赋。又因此冒犯上司而长期不得升迁。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朝廷开修宋、辽、金三史,次年,杨维桢上《正统辨》,颇得欧阳玄的赏识。至正十年(1350),改任杭州司务提举,不久改任建德路总管府推官。至正十五年(1355)升任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但因兵乱而未赴任,先是避居钱塘,后因得罪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尔,徙居松江。张士诚据吴中,累招之,不赴。明初,应诏赴京师修礼乐书,至京仅百日,因肺疾作,遂返回松江,不久便去世,年七十五。
由于杨维桢从小聪颖好学,又经过十多年的苦读和广采博收,不仅善作时文,而且擅作乐府古诗,雄奇怪丽,自成一体,世称“铁崖体”。为世人所推重,如宋濂为之作《墓志铭》称:“元之中世有文章巨公起于浙河之间,日铁崖君,声光殷殷,摩戛霄汉,吴越诸生多归之,殆犹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余年乃终。”一生著有《春秋合题著说》、《史义拾遗》、《东维子文集》、《铁崖古乐府》、《复古诗集》、《丽则遗音》等。另外,他又博学多艺,谙熟曲律,口吹铁笛,唱曲歌舞。他在寓居苏州期间,结识了顾瑛,成了顾瑛玉山草堂雅集上的常客,与赵孟烦、倪元镇以及昆山腔的创立者顾坚等人作曲唱和。《全元散曲》收其北曲小令、散套各一。其中他所作的南【双调·夜行船】《苏台吊古》套曲,后被梁辰鱼借用在《浣纱记·泛湖》出中。他曾为一些曲集作了序跋,在这些序跋中,提出了自己的戏曲主张。二、今乐府论曲是元代新兴起的一种音乐文体,曲有散曲与剧曲之分,元人常将散曲称为“乐府”或“今乐府”,以表明这一新产生的音乐文体与前代乐府诗尤其是宋代文人词的渊源关系。作为好作乐府诗的杨维桢来说,4~\'dz十分注重曲与传统诗词的渊源关系。他在考探曲的起源时,将曲(今乐府)的最早源头上溯到先秦的《诗经》,而后又变而为骚、赋、曲引、歌谣,又变为长短句体的词和曲。如《渔樵谱序》日:《诗三百》后一变为骚赋,再变为曲引,为歌谣,极变为倚声制辞,而长短句平仄调出焉。至于今乐府之靡,杂以街巷齿舌之狡,诗之变盖于是乎极矣。
在这段论述中,杨维桢将从《诗经》到曲(今乐府)的演变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从《诗三百》到骚赋,这是第一次变化,《诗经》的文体为齐言体的四言句,而骚赋则为杂言体,因此,这第一次演变是由齐言体转变为杂言体。从骚赋到曲引、歌谣,这是第二次变化,曲引、歌谣皆为齐言体,因此,这第二次演变则是从杂言体转变为齐言体。从曲引、歌谣再演变为长短句平仄调,即词,这第三次变化,则又从齐言体转变为杂言体的长短句。第四次变化则是从长短句的词,演变为同为长短句杂言体的曲(今乐府)。这四个演变阶段,一是从文体上来看,是齐言与杂言两种文体的交替演变,即先是从齐言到杂言、再从杂言到齐言、又从齐言到杂言,而这种文体上的交替演变,不是简单的轮回与重复,而是使得诗体文学在文体上更高级的发展与成熟。杨维桢认为,其中长短句体的词曲的产生,相对于传统的诗体文学来说,是发生了“极变”,即与以前的诗体文学有了质的变化。二是从创作方法上来看,分为“倚辞制声”与“倚声制辞”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倚辞制声”,就是按照歌词的字声来制腔,而所谓“倚声制辞”,就是按照既定的格律填词,故作词又称填词,杨维桢认为,“倚声制辞”是“长短句平仄调”即词调产生的关键因素。三是从语言风格上来看,有着雅与俗之变,如从词到曲,词的语言文采典雅,而曲的语言通俗本色,多“杂以街巷齿舌之狡”,即多有俗语口语。通过对诗体文学的流变过程与曲的渊源的考述,也指出了曲在文体与乐体上的特征,即一是由于其是继词而起的,故也是采用了“倚声之辞”的创作方法;二是在语言风格上,不同于词的雅,而具有俗的风格。
其次,杨维桢对今乐府的创作提出了要求,确定了文律兼美的美学标准。如他在《周月湖今乐府序》中指出:士大夫以4\"-乐府鸣者,奇巧莫如关汉卿、庾吉甫、杨淡斋、卢疏斋,豪爽则有如冯海粟、滕玉霄,酝藉则有如贯酸斋、马昂父。
其体裁各异,而宫商相宣,皆可被于弦竹者也。继起者不可枚举,往往泥文采者失音节,谐音节者亏文采,兼之者实难也。夫词曲本古诗之流,既以乐府名编,则宜有风雅余韵在焉。苟专逐时变,竞俗趋,不自知其流于街谈市谚之陋,而不见夫锦脏绣腑之为懿也,则亦4-r~y,.于今之乐府可被于弦竹者哉!在元代,关汉卿等皆以今乐府著称,为人们所推重,这些曲家所作的今乐府都能做到文采与音律兼美,语言各具风格,或奇巧,或豪爽,或蕴藉,体裁也各不同,或小令,或散套,音律上又都合律依腔,宫商相宣,可被于弦竹者,用于演唱。而在关汉卿等曲家之后,虽“继起者”众多,“不可枚举”,但他们所作的今乐府则很难做到文律兼美者,“往往泥文采者失音节,谐音节者亏文采”,因此,杨维桢发出了“兼之者实难”的感叹。
在《沈生乐府序》中,杨维桢也提出了“辞简”与“调严”的主张,并对张小山与刘廷信的曲作作了评述,日:我朝乐府,辞益简,调益严,而句益流媚而不陋。自疏斋、贯斋以后,小山局于方,黑刘纵于圆。局于方,拘之过也;纵于圆,恣情之过也,二者胥失之。
在他看来,“辞益简,调益严”,这是“乐府”的主要艺术特征,但自卢挚(疏斋)与贯云石(酸斋)等前辈曲家之后,辞与调兼得者不多。如张小山的曲作因其拘于曲律,绌词就律,故缺乏文采,拘谨而不生动;而黑刘即刘廷信的曲作则因其过于恣情自娱,故虽有文采,但失之圆滑。杨维桢认为,这两者皆失之。
关于今乐府的语言,杨维桢提出,须“流媚而不陋”,认为曲与词相比,虽已“杂以街巷齿舌之狡”,流之于“靡”,但既然曲是由词演变而来,而且仍有“乐府”之称,因此,其语言还是应该保持词的“风雅余韵”,而不能俗而文,否则便“流于街谈市谚之陋”了,如他指出:夫词曲本古诗之流,既以乐府名编,则宜有风雅余韵在焉。苟专逐时变,竞俗趋,不自知其流于街谈市谚之陋,而不见夫锦脏绣腑之为懿也,则亦何取于今之乐府可被于弦竹者哉!可见,他虽然看到了曲较词为俗,但在他看来,曲的俗不是俚俗之俗,而是既本色又富有意蕴之俗,就像关汉卿等前辈曲家所作的曲作,虽本色通俗,多用民间口语俗谚为曲文,但富有意蕴,是经过作家提炼加工过的“俗”。因此,他认为,若曲家“专逐时变,竞俗趋”,那就会“流于街谈市谚之陋”,即俗而鄙俚,这样的话,还不如“锦脏绣腑”,即文采典雅之为懿也。
又《渔樵谱序》日:
嘉禾素庵老人过予云间邸次,出古锦朴一帙,日《渔樵谱》者,凡若干阕。虽出乎倚声制辞,而异乎今乐府之靡者也。
《渔樵谱》是素庵老人所作的散曲集,其所作的曲调以及创作方法虽“出乎倚声制辞”,即也为长短句平仄调,但其语言却具有文采,而无“今乐府之靡者”。
三、情性论
杨维桢论诗重情性,他认为,诗品如人品,诗品的好丑高下,取决于诗人的人品的好丑高下。如他在《赵氏诗录序》中指出:评诗之品,无异人品也。人有面目骨骼,有情性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亦然。
《风》、《雅》而降为《骚》,《骚》降为《十九首》,《十九首》而降为陶、杜,为二李,其情性不螯,神气不牵,故其骨骼不庳,面目不鄙。嘻!此诗之品,在后无尚也。下是为齐、梁,为晚唐、季宋,其面目日鄙,骨骼日庳,其情性神气可知已。嘻!学诗于晚唐、季宋之后,而欲上下陶、杜、二李,以薄乎《骚》、《雅》,亦落落乎其难哉!然诗之情性神气,古今无间也,得古之情性神气,则古之诗在也。然而面目未识,而谓得其骨骼,妄矣;骨骼未得而谓得其情性,妄矣;情性未得,而谓得其神气,益妄矣。
由于诗人的情性决定诗作的风格与品位,因此,他指出,若后人要学习前辈诗人的诗作,这是学不到的,这是因为人的情性各有不同,如他在《剡韶诗序》中指出:或问:“诗可学乎?”日:“诗不可以学为也。诗本情性,有性必有情,有情必有诗也。
上而言之,《雅》诗情纯,《风》诗情杂,下而言之,屈诗情骚,陶诗情靖,李诗情逸,杜诗情厚,诗之状,未有不依情而出也。”杨维桢在论曲时,也十分重视作者的情性。他认为,曲家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风格,也是由其人品决定的,如《沈氏今乐府序》日:今乐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然而媒雅、邪正、豪俊、鄙野则亦随其人品而得之。
阅读期刊:《戏剧艺术》
《戏剧艺术》刊登戏剧理论和戏曲研究成果,介绍外国戏剧理论与作品,发表舞美、戏剧导演与表演艺术、戏曲教学、影视艺术等方面的学术论文。被北大1992版核心期刊、北大1996版核心期刊、北大2000版核心期刊、北大2004版核心期刊、北大2008版核心期刊收录。

 >
>